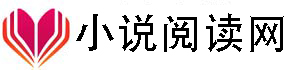50-60(2/32)
的时候,明明敢和先帝叫板,阻止她被送去和亲。可现在,皇位上的人换成了他,他反倒成了强迫她的那个人了。赵明臻推开了赵景昂的手臂,无声地掉了一会儿眼泪,似乎也想起了什么。
良久,她才终于开口,问道:“疼吗?”
赵景昂慌忙回过神来,胡乱答道:“不疼,我……”
见赵明臻抬眼看他——看他颊侧那道掌痕,他垂下眼,轻声道:“疼的。阿姐,我做错了。”
听他喊疼,赵明臻别开了视线,道:“你是皇帝,你怎么会有错。也是我冲动,一会儿,你让戴奇给你找些冰块敷一敷。”
她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,这记耳光落得严严实实,这会儿已经有些肿起了。
赵景昂的脸上像被火烧了一样,却不只是因为那一巴掌。他抿了抿唇,道:“是我错了,该吃这打。”
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这些年读的书、受的教,若非阿姐打醒我,我竟浑都忘了。”
他这么快就低了头,赵明臻反倒不适应了起来。
她抿了抿唇,眼泪已经止住了:“你高估我了,我没想这么多。我只是觉得,水能载舟亦能覆舟,若不把百姓放在眼里,翻覆也是早晚的事。难道真只凭朝堂上这些所谓的大人物,就能撑起整个大梁吗?”
赵景昂深吸一口气,道:“我知道了,阿姐。”
他深深地看了赵明臻一眼,随即一字一顿地道:“以后,阿姐莫再说什么要杀要剐的话了,听着实在叫人难过。”
“不论发生了什么,我都不可能会对你动手的。”
他大概不想等她回答这句,话音未落,便转身走回了御案前。
“开弓没有回头箭,打,那就要打胜仗。”赵景昂提起笔,道:“阿姐,这封旨意,便由你带给燕将军吧。”
——
一夜未眠,燕渠的脸上,却看不出多少困倦的痕迹。
连他胯。下的这匹杂色马也是。
物似主人型,明明它也一宿没好歇,先后被两个人骑来骑去,这会儿竟然还有点亢奋。
燕渠察觉到了,轻笑一声,拍了拍马脖子。
天色已然破晓,微茫的日光渐从远山后升起,城北大营的围帐就要映入眼帘,燕渠很快正色敛容,神情肃然地下了马。
他手持虎符和圣旨,当即便入营与城北军的头领相商,随即便开始清点人数,在校场动员部署。
燕渠行事一贯雷厉风行,更不必提前线军情已是十万火急。还未至傍晚,三千人的大军便已整饬完备,亟待出发。
就在这时,亲兵来报,言道皇帝竟已出京,这会儿已经抵达了城北大营,说是来劳军送征。
皇帝亲自来送,重视程度可见一斑。尽管燕渠深感意外,还是很快起身,率部亲迎。
日光正盛,仿佛昨夜的阴霾从来不曾存在过。赵景昂正骑在一匹红棕色的高头大马上,橙黄的阳光流溢在他袍服间,显得格外华贵。
在他身后,还有其他几位文武大臣,以及……
察觉到燕渠的视线投来,赵明臻轻轻哼了一声,昂起了下巴。
“参见陛下——”
见众武将下马行礼,赵景昂眉眼平和地叫住了他们,随即朝所有士卒朗声道:“不必多礼。军情如火,朕没有闲篇要讲,只一句,保家卫国,论功行赏,万望诸位,早日归营。”
皇帝金口玉言说的“论功行赏”,那自然是十分振奋人心。
他似乎还有话想对燕渠讲,稍加思索了片刻后,还是调转马头,